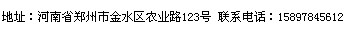刘恒关于电影的十五对反义词
编者的话
从年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黑的雪》改编成电影《本命年》算起,刘恒入行成为编剧已33年。在刘恒看来,电影是充满力量的,它的力量从政治、社会和艺术三个部分迸发,相互缠绕而成为电影的“形而上”,相对的,另外两个层面则是“形而中”和“形而下”,刘恒将自己对电影的灵感化为这上中下三个层面的十五对反义词。
今天我们节选刘恒在厦门青年导演训练营的演讲《永恒的艺术力量》中关于电影的十五对反义词的论述,与大家共享。
··········
永恒的艺术力量
文
刘恒
刚才说了电影的三个力量。政治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如果让我概括以上表述的共性,我觉得它们都涉及了“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你们可以查,到百度里可以查,它是《周易》里的用语。它跟形而上学还不是一码事。形而上为道,道就是道家的那个道。道是神圣规则,是精神层面的,是看不见的一种东西。形指的是人,形而上指的是在人之上的那个东西,天上的东西。
除了刚才讲的形而上,还有两个形,一个是形而下,一个是形而中。形而下为器。器就是工具。你所有的力量是要靠工具来展示的。你必须熟悉那些手法、规则和套路,它们像数学的公式一样饱含逻辑,是对行业规律性的总结,你的所有创新都离不开这些工具。编剧有一大套,导演有一大套,制片人有一大套。形而下就是逼你落地,你要光在形而上上面飘着,没有形而下支撑的话,就是空中楼阁,不堪一用。
最后是形而中。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形而中则为心,心脏的心。形而上是理念,形而下是手法,形而中指的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品质和状态。后者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上。上中下,天地人,人是最宝贵的。
昨天晚上考虑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临时生发了一些想法,记在笔记本上。我看能不能试着用这个新的瓶子,把那些旧酒给装进去。这个想法我曾经开过头,但是没有像昨天那样,好像一下子就有了灵感,一下子就贯下来了。我想用15对反义词,来分别拆拆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的具体意思。
关于“形而上”的五个反义词
先插一句题外话,我在某个当代政治家的著作里接触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在我的知识范围里。他简述了“概念的兑换”。他用了“兑换”两个字。概念兑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概念可以代替另一个概念。通过兑换可以使原有概念更丰富、更具体或者更生动,有多种延伸的可能。比如说人这个概念,可以兑换成高级动物。所以当我们说到形而上的时候,可以将它兑换成主旨。我为它准备了五对反义词。
第一对反义词是生死。生和死是生命最重大最辽阔的主题,并不局限于艺术。尤其是死亡,对艺术影响之甚,无出其右。我前些日子到乌镇戏剧节,跟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的名导演名演员对话,一场谈契诃夫,一场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契诃夫的时候,我强调了他是一名肺结核患者。肺结核在19世纪是不治之症,跟艾滋病和癌症一样,得了基本就活不了了,苟延残喘。我说过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就两类人,一类肺结核患者,一类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个是我开玩笑的总结,但确实很多顶尖的作家都得过这两种病。鲁迅是这个病,卡夫卡是这个病,很多都有肺结核。你们可以广泛涉猎作家的传记,看看有多少人得了肺结核。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他们对人类产生了非常沉重非常阴郁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更极端了。他16岁的时候妈妈死掉;17岁的时候,爸爸死掉。25岁的时候,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被沙皇判处死刑,别人都给毙掉,却把他放了,等于死了一回。熬到40出头,老婆和哥哥同一年死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是一个烟草商,经济宽裕,一直支持他写作。这些死亡摧残了他的神经,也极大地成全了他的文学创作。
所以我觉得死亡所焕发出的那种能量,作为一种创作资源,是第一位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所有伟大的作品是不是都跟它有关系?我们可以凝视自己的生命本身,从上升期到衰落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消耗下去,像燃尽一根蜡烛。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应该是艺术的起源,就像宗教的起源一样。艺术起源于巫术,巫术的实质无非是人类幻想永生,想挽留生命,想永久地留住它。但是你留得住吗?留不住啊。古代的名人愿意把自己的字刻在岩壁上,人死了让那俩字儿替他活着,算盘打得很精。
文学作品有这个潜在的功能,就是通过精神层面的努力,使自己的生命以某种方式得以延续,而且它也确实能起到这个作用。如果作品足够伟大的话,确实能够无限地延续你的生命,延续你的精神生命。作为你个人的一个符号,它可以长久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这是形而上的第一对反义词——生死。
第二对反义词就是爱和恨了。刚才好像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恨从什么地方来?从竞争中来,从人和人的冲突中来,从人和人永恒的利益分野中来。一个人永远无法代替另一个人。你哪怕与另一个人有血缘上的亲密联系,你也仍然是另一个人,你的利益无法跟他完全重合。所有的恨是从这儿来的。因为利益不同,所以在争夺资源的时候,彼此是以个体出发,大家必然是彼此相争的。在这个残酷的过程当中,恨就积累起来了,而且印证了竞争本身的意义。
爱和恨这一对反义词可以从以上角度来理解。爱就更不用说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的源头和尽头都是利益,无利不争,爱是用来兑换的,兑换失败就因爱生恨了。是不是这样?历史中有很大一部分战争,那个打了多少年这个打了多少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我觉得人类的战争持续时间最持久的,而且是无孔不在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这个战争始终在酝酿、在爆发、在延续、在变幻花样。但是雌雄大战是爱的源泉,也是一个恨的源泉。毫无疑问,它就是艺术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仓库,权重仅次于生死这一对反义词。
第三个反义词是善恶。我还是接着刚才那个观点讲,不知道我能不能自圆其说。竞争造成痛苦,竞争给人类带来伤痕。人世间的所有痛苦与此有关。但是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我为了在竞争当中占据主动地位,我要恶,我要像狼一样参与竞争,我要把我的牙齿磨得更锋利,而且要为我这种残暴找到合理性,找到理由。我们大量作品不就是在干这个事儿吗?那些暴力电影怎么来的?那些黑色小说是怎么来的?那些阴暗的小说是怎么来的?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而且应该是更主要的观点,觉得这样没有出路。大家都变成恶狼之后,彼此野蛮厮杀之后,人类的路会越走越窄,越走越窄。一个人的痛苦,蔓延开来成为大家共同的痛苦。
大家会被这个痛苦的深渊给埋葬,不能恶下去,要善,善是出路。宗教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儒家学说不就是这么来的吗?道家学说、基督教、印度教、犹太教……各种各样的宗教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就是希望寻找一个善的方向,举起善的旗帜,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结果就是,善恶之念始终在打架。
所以,每个表达者在自己的艺术创作里都会给善恶一个恰当的位置,它跟你对生活的感受,跟你个人的经历,跟你所学到的知识,跟你这个人的品位都有紧密的联系。你最后在善恶之间达到怎样的平衡?我觉得这是展示你水平高下的一个标志。有的人会失去平衡。
我列了数十个反义词,只给形而上这一部分挑拣出五个,不知道挑得准不准。下一个反义词,我把它概括为祸福,就是古人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什么福兮祸所依啊,祸兮什么什么的。福和祸的关系结构,就是人类命运和个体命运的图谱。
祸展示的是生活的不可预测性,而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是正常的,是必然的。有的时候,因为心理脆弱,我们妄图把这种必然的不可预测性变成可预测的,我们去求神拜佛、寻仙问道。那些骗子给你许诺这个许诺那个,说你要升官了,说你要发财了,都是心理的痒痒挠。这个祸带来的恐惧和焦虑,也是艺术的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祸,大大小小的祸,大大小小的失意,大大小小的挫折,在人的一生当中是贯穿始终的。你最得意的时候,哎!可能家里出问题了,夫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最信心百倍的时候,觉得自己能力特别强的时候,突然患了不治之症了。跟朋友肝胆相照,哎呀,突然这个朋友背后捅了你一刀……正高兴呢,手里扎了个刺儿怎么都拔不出来。总之,大大小小的祸在生活里随时会出现,也会随时在我们的艺术表达里在电影里出现。艺术展示的是我们对生活不可预测性的态度,也是对每一个都会遇到不可预测性之祸的观众的一种抚慰,乃至是一种恐吓,或者就是一种鸡汤式的灌注。你总是要表达你对祸福的一个态度,以此来跟观众交流。
我觉得如果你认识深刻,你表达得生动,有可能会减缓被不可预测性闹得很焦虑的某些人的沉沦,也就是说你会给观众创造某种精神利益,你的这个活儿就比算命先生那个活儿高级得多了。
再说到福,在艺术里它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写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涉及到这个主题。艺术剖析幸福的时候,给人们展示的究竟是什么呢?展示的是幸福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哪有十全十美的幸福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幸福都是相对的,而且幸福应该是奢侈品。他不是像每天早上那个豆浆油条,随时掏几个小钱就来了。没那么简单,而且坦率地说,幸福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陷阱,至少是个心理陷阱,每个人都有机会掉进去。我在生活里定一个指标,我觉得我达到这个指标就幸福了。但是你这个指标不是恒久不变的。我挣了万,我能不能挣0万?挣0万还不够花,挣一个亿呢?你的幸福指标像皮筋一样,随时拉,随时让你处于不满的紧绷的状态。我觉得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你给自己定了一个幸福的指标之后,你达到幸福的能力不够。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公式,来自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你的幸福指标跟你追求幸福的能力,一旦不能成正比的时候,这个差,就是你的痛苦值。这个差有多大,你的痛苦就有多大。你说我幸福定的刻度是10,但是我实现幸福的能力只有两个刻度,你的痛苦值就是8个。你的幸福值是5个,你追求幸福的能力值是3个,只有两个差,你的痛苦值就相对小一些。当然你最好正好对上,我的幸福指标只有0.5,我追求幸福的能力也是0.5,甚至能达到1,能力超过我的指标,那我的幸福感就很强了。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演员合影
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艺术创作的主旨会频繁涉及这个问题,会涉及你对幸福的理解和展示,你自己的职业状态本身就带有这个性质。在座的这么多人来听讲座是为什么呀?不就是想让自己的活儿干得更漂亮吗?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能够被我所用,吸收过来或者至少给我一点儿启发,不就为了这个吗?我自信我在这里输出信息的方式,对每个人是公平的,说的话大体上都是每个人能够理解的话。假设我真找到了一条真理,实打实地扔给你们了,每个人都拿着真理出去……信息传递的外观看起来是平等的吧?一出去差距就出来了,一上手差距就肯定出来!那位不费力气玩着就把活干了,干得还特别漂亮。另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无所获,驴唇不对马嘴,都有可能啊!你怎么办?只能自我调节自我领悟,谁比谁傻呀?谁又比谁聪明?大家智力都差不多,都是中长人。极其优秀的那种天才,过目不忘灵魂出窍的人很少。极其蠢笨的人,钻牛角尖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我们最后获得的成绩,会有极大的差距。而且坦率地说,通往最顶端的,通往顶峰的那个道路,那个梯子非常狭窄,有无数的人在攀爬。你凭什么捷足先登?不得不再次说到屡屡提及的那个中心词——竞争。大家在争,大家为了自己的幸福,在争这个梯子,争自己的站位,争自己对别人的摧毁能力,争自己的智慧智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全面的身心竞争,当然还有客观机遇,说不定你正取得一个好位置的时候,来一阵狂风暴雨把你给打下去了,人家却风调雨顺。或者是人家突然遇到一个仁者宁肯把自己舍掉,也要把他推上去。有外力的协助,有机缘巧合,但是最后拼的,还是你自己的智慧。在我设置的所有反义词里边,处于最高位置的,就是智慧和愚蠢。你所有的艺术能量,就在这一对反义词之间摇摆,在智慧和愚蠢之间摇摆。不幸的是,人往往容易被愚蠢俘虏。你觉得自己充满理性,认识到那儿有一个陷阱,而且前面有好多人已经掉下去了。理性和逻辑都告诉你,决不能从那儿走,最终你还是掉下去了。艺术的车祸比比皆是,这个真是没有办法。
在艺术的领域里,理性不能解决问题,这跟政治不一样,跟社会问题也不一样。理性和逻辑,不足以挽救你的艺术生命。拿什么能挽救呢?你能依靠的,就是你长久积累的艺术才能。没错,就是长久的积累,是日复一日地对外部知识细致的、充足的观察与吸收。你要持之以恒地阅读。阅读对象仅仅是书本吗?你还要阅读现实啊!阅读你的人生经验,阅读你自己的心声,甚至阅读你内心隐秘的人生痛苦。你有视觉,你有听觉,你有触觉,你一直在坚持阅读吗?未必,因为这太令人厌倦了。放弃阅读,是你才华流失的第一步,是你对愚蠢无感的第一步,你已经不自觉地退出竞争了。
智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律。所谓自律,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说起来或许有点儿鸡汤的味道。生活里诱惑非常多,你的注意力会被各种有趣的事物吸引,时间肯定不够用,那么你准备将多少时间投入到你所喜爱的这个职业当中去呢?我觉得所谓自律,就是对你自己所掌握的有限时间的持久管理,有效的管理。如果再兑换一下概念,时间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你的生命由时间构成,你管理时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管理你的生命。假设你的生命是一支将要燃烧70年或80年的蜡烛,在它燃烧的时候,你想用这个小火苗这点儿热量去干些什么呢?这是可以由你自己来控制的。当然,绝大部分人控制不了,随便烧吧,爱怎么烧怎么烧吧。喝点小酒、打个麻将、睡个懒觉、扯扯闲篇儿、泡个妞……有无数的世俗的快乐都在诱惑你,丧失自律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谁成功突围了呢?就是那个严格自律的人,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进行严格管理的人。但是有可能,你再怎么严格你也成功不了,但是你要想成功你必须得严格管理。
如果你想让你的艺术创造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刻下一道深深的痕迹,让它永久流传,成为经典的伟大的作品,你就必须过一种严格自律的生活,必须把你的生命作为一种燃料,作为一把柴火,扔到你热爱的事业里去,让它充分燃烧!如果做不到这一步,靠一些浮皮潦草的小聪明去将就你的职业,就算你有一些才华,你的生命也燃烧不起来。我见过很多这样颓唐的人,电影界文学界都有,最终他们大抵是把珍贵的才华扔到茅坑里去了。
我又扯远了。智慧和愚蠢不算,第五个反义词应该是新与旧。不论是生活还是艺术,新旧冲突无处不在。“新”被“旧”阻碍,或者“旧”被“新”打败,都会形成悲剧。它们是生命自身的一个缩影,世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会变旧,就跟婴儿生下来必然会走向衰亡一样。在座的“90后”,你们是早晨的太阳,一直在往上走,往12点的方向走,你会误以为你的生命曲线一直是向上的。但是你别美,只要过了12点,你就该往下出溜了。你原来往上走是有阻力的,过得很慢,往下走可就加速度了,拦都拦不住,眨眼就夕阳西下了。我今年66岁,我可以作证,三十而立的豪迈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生命的衰老非常快,这个速度无法遏制。
“80后”“90后”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就要用这种心态来对待自己的职业,在它没有快速下滑之前,在黄金上升期的这个段落,充分地锤炼自己的职业技能,充分地培育自己的艺术素养。谁比谁差?大家就争呗。牙关咬得最紧的那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掌握得最紧凑的那个人,离成功最近!
关于“形而中”的五个反义词
形而上已经讲了两个小时,就此打住。形而中和形而下各有五个反义词,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自己去分析。
第一个反义词是悲和喜。从外观看,悲剧,喜剧。从内里去分析,是悲伤的情绪和喜悦的情绪。我最近看了《小丑》,它把悲和喜的感觉用一种极度夸张的方式融合在一块儿。我们通常认为笑肯定是喜悦才笑,但是小丑那个笑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的笑里边隐含着巨大的悲哀,冲击力非常强。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完全写实的描绘,他是一个寓言式的、夸张式的强调。它体现了人类情绪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悲喜交织。就像弘一法师死前写的那几个字,悲欣交集。最好的艺术表达形式就是这种悲喜的交集与融合。欧洲戏剧界的人是怎么比喻的?悲剧是秋天,喜剧是春天。中国古人好像也是这种境界。
下一个反义词跟形态有关系,就是信和疑。仁义礼智信的“信”,怀疑的“疑”。信和疑要从外观看,这次国庆节的献礼影片都是属于“信”这类的。主旋律,正能量,正面,都是信的问题。目的就是要把一种“信”的信念传递给你,让你也相信它,接受它。
我觉得《圣经》完成的就是这个事情。《圣经》也是由小故事组成的,也有人物,也有故事,也有对话,但是它就取得了至高无上的“信”的地位,让这么多信徒膜拜它。我们无神论者觉得很荒谬,耶稣怎么会那样呢?死了以后又复活,又从地底下爬出来?它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空灵故事,却征服了大量信徒。所谓的主旋律,所谓的正面概念的传输,所谓的英雄的旅程以及牺牲与奉献,等等,想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设法让接触到我们信念的那些人,由衷地信服它,理解它,赞同它。优质的电影真的就具备这种打动人心的力量,让你在某一瞬间心里一暖,觉得特别的惬意,或者特别的心酸。这就是“信”。
还有一个“疑”,疑是什么?疑是批判性,批判性这个幅度是非常宽的。你可以是反社会的批判,可以是出于理智的批判,也可以是疯狂的、狭隘的、片面的批判,都可以打着这个“疑”的旗号。或者你可以把前面分析过的善恶中的恶拎出来,打着恶的旗号进行“疑”的操作。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打着“善”的旗帜来做这个“疑”的事情。《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对准了生活里的阴影,就是这么干的。电影应该强化这个功能,对现实的深入剖析是有出息的艺术工作者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老了迟钝了,必须寄希望于你们年轻人的敏锐了。
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社会对慢粒白血病人等特殊群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