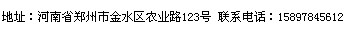李国华还活着
昨晚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
看到了某中学数学老师段向阳猥亵学生的相关微博
其遭遇与房思琪如此相似
决定删减后重发这篇推送
当时配的音乐也没有改
千千万万个李国华还活着
而他们站立着的阴影下
是无数房思琪破碎的心灵
很多人可能不太敢看房思琪的故事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林奕含的绝笔
我真正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她还是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我重发这篇推送
目的是想让不太了解这个故事的人
能够产生哪怕一点点的共情
决定在这里只放上三小篇
类似于她的博客
但脱离于小说之外的部分
一篇雏形
一篇婚礼致辞
(一定要看,网上有视频版)
另一篇补充说明
希望大家能听完她的声音
林奕含发表了网志进学解
林奕含·年4月14日
(前言:《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我一直想写出来的小说,很多年行走坐卧在脑子里涂改,却是直到这篇散文,才真有了雏形。这是房思琪正式的起点。写于年8月。如果你于小说共感,也愿意分享这散文,我会感激的。)
我休学了。上学期,被二一之前,写信给老师们:「我不能阅读。听起来很怪异,但是是事实,非常抱歉。」附上诊断书。老师说诊断书不清不楚,暗示我从哪里搞来这一张纸。这是中文系超人的浪漫,好莱坞的超人,不是尼采的超人。
第一次住精神病院,带了莒哈丝、贝克特、莎士比亚。读完一排书,还不能出院,只好背十四行诗。经过一首诗,抬头,铁栏杆在温吞走廊上的影子偏斜一些,依旧整齐、平等,像中共文革合唱团的两张连拍照片,模仿死神怀表指针的摇晃。人一死,就不会晚老。
有个病友厌食症,森森整个人像髑髅镶了眼睛。镶得太突出,明星的婚戒,六爪抓着大钻。一只戒指在南半球,一只在北半球,还是永以为好。没看过两只眼睛如此不相干。她总把饭菜藏在口腔,进厕所吐掉,总被发现,总被骂。她喜欢偷我的零食,艳色的零食包装窝在她宽绰的粉绿色病袍里,她像张考卷被荧光笔恶意涂上一杠,遂没有人在乎原来几分。看护阿姨骂:「妳哪来的巧克力啊?」她会指着我,枯手指光样延展,摸我一把,看穿我。我说:「啊,那是我给森森的。」我喜欢让她偷,不是共谋的快感,或谅人的自满,喜欢她不垢不净地指出我,透明手指沾着黑巧克力。在医院,我们不是女儿,学生,职员,妈妈,而是某种病在某段疗程的病患。
她老叫我念书,自己在旁边絮叨:「妳好瘦,好漂亮,我想瘦,想漂亮」,莎士比亚是伴唱,或是男人开着电视遮住身下的小女孩。她在莎士比亚里很安全。她的指头骨节像电线上有麻雀,高高箍着手指,透白皮肤扯着,可以听见饥饿的青色小血管被拉紧,一跳一跳吞口水的声音。偶然看见她脱衣服。上身像木板绷上帆布,平整,无生意。帆布只画上两只小眼睛,油彩也不大方,肚脐是下方一个破孔。显然画家穷,画人脸的顺序也怪。艺术往往躲在精神病里点滴地自杀。一看,强烈地感到:森森活不久了。更奇怪的是我不太惊讶或伤心。
她常吵闹,泼饭盒,米粒天花乱坠,她咆哮:「我要变瘦,变漂亮,变瘦,变漂亮!」像卷录音带,齿轮嗤嗤吞吃黑舌头。被扭打进保护室。我没有进过保护室,只看过病袍飘飘然装着森森出来。一时,外头的灯投入一竖笔光线,蜗房拉开一袭平行四边形的光明,灯光很有慈悲,泄漏,与八卦的意味。保护室的地板,天花板,四壁,都是粉绿色泡棉,像个好梦。我想过,除了一直抠泡棉,吞下去,不太可能在那里自杀。或是他们说的,「伤害自己」。
护理师最喜欢对我说:「真乖,又在看书。」森森是不乖的,我是乖的。
精神病院无所谓时间。洗澡超过二十分钟会红灯,早餐时间吃早餐,午时吃,晚上吃。甚至有早操,壮丽人声配着升平音乐,成群手臂鱼嘴开合。有的手矗着毛发,或云云浮出青筋,或是两束白骨。像最逼真的共产庄园,但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不是理想,而是幻灭。
在院里写日记,院里最多的就是时间,因为院里没有所谓时间。
「听说你说:『妳是——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知道你在双关小女生的私处,我是多么恨自己背古文的习惯。
「你说:『妳一身都是风景。』——这话多俗!很替你羞惭。
「你引阿房宫赋:『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泛爱』不是这样的。最讨厌你说『慈悲』。」
上学期被二一,因为期末考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小女生。我在二楼,雨棚如乌云,眼神从佛教哲学的正道溜出去,遥见你颜楷般筋肉分明的步态,她很矮,仰望你,像楚辞的那章——天问。我可以看见她的脸,鸭蛋脸游离于寤寐,像还在床上,不是眼睛在张望,而是粉红睡痕。战兢的媚态,我太认识了。一时间欲聋欲哑,恨二楼跳不死人。
那天起,我不能看书了。坐拥她们,如果你与文学切割,承认兽性,或许我会好过一点。但不,你一面念《诗》,一面插着蒹葭。抽出来,蒹葭沾着白露。白露如落日,满面通红。夙夜匪懈的白露,血色的白露,时差的白露。有钟摆夜光着在她体内敲出正午的钟点,她的身体一向乖巧,脏腑迷惑,筋膜鼓噪,它们不知道是谁迟到又早退。脏器一个挨着一个,拖累她,锚坠她,把她从公寓阳台翻覆,泼下去。她的身体里一定很暗。
你对她们总一开始就谈文学。她在升学的压力里摸黑行路,你的一口典故如阳光突然刺穿眼皮,如满汉全席铺天盖地,交错觥筹,她醉了,理性渐渐褪色。她总扎着精密的马尾,而你来回看她,像背诗。后来,你对她说了一句话,那话像个刚粉刷、没有门的房间,墙壁白得要滴下口水,步步进逼、压缩、一句话围困她的一生,你说:「我爱妳,但我也爱培培。」你她当场分别了。当然后来她明白培培亦是被污的。
说你既文既博,亦玄亦史,原来,玄的是有礼离席,是泛爱众「生」;史是你包包里的小册子。小册子里,芬的,芳的,郁的,小女生名字,并肩如伍,被纸夹杀,喷发异香。你说书,说破她们。星期一芬日,星期二芳日,等等,生命如此丰满、规矩,在岛屿上留情,像在家里梦游,一点不危险。你给她什么,为的是再把它夺走,你拿走什么,为了高情慷慨地还她。
多年来我书写那部当代罗莉塔与胡兰成的故事,我像只中枪却没被拾走的动物,宁愿被吃,也不愿孤单死去。写文章屏蔽又回护官能,伟大的心灵围观、包庇我的噩梦,抬举灵魂,希望臭酸肉体鸡犬升天。说好听是净化,说实在,就是美化。像侧睡,你形容蓝花纹的被子服贴她,「像个倒卧的青花瓶」。如果你的兴趣不是插花多好。如果你不把自杀当成最伟大的恭维多好。如果一个女生自杀了你就收手多好。最可怕是揣着老师的身分一面犯罪。学问何辜?书页多么清白?
我恨我迷信又说嘴:国中开始读吴尔芙。如果不是逐字引用作主体的材料,锻造我的尊严与欲望,文学也不能让我墨劓刖宫、笞杖徒流地幻灭。有老师问我「不能阅读」是什么——《左传》、《史记》、《楚辞》,其实不用写那么多,人间与生命的真相或内核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彻底描述:花了几年知道这叫奸。
森森在我出院后死掉了。电视外,隔着马赛克,也认出她来。没有人知道,我每天拉开领口,望下看见乳头外一圈齿,想沿着齿痕的虚线剪开,把性征丢掉。森森死了,她是不乖的,我是乖的。我是乖的,因为幻觉不会从眼睛投射出来,播放在建筑物的侧脸上,因为从小到大,别人游戏时我总在看书,连在精神病院也一样。
林奕含回复:我觉得我要解释一下:我当然希望读者痛苦,也感谢共鸣的读者,但我不觉得人应该高估自己的同理心,人都是健忘的,读了很痛没错,但你会痛多久?这痛会改变你吗?人面对那么大的创伤应该谦虚一点,就像我不可能用意志力,只能看医生、吃一堆药,药物是我谦卑的方式。4月13日18:40林奕含回复:那我在这里因为中文主被动不分语法的关系,没有说清楚,这个伤痛对我是直接的,对读者,用那句话——他们是在旁观他人之痛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小说里思琪说「没有人应该经过这样的痛苦而变成更好的人」,那个经过是直接的;但是读者,他们属于伊纹对怡婷说的,「不必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是被动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是我语法上没表达清楚。然后我们不要在这里讨论,好赤裸。林奕含婚礼致辞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娘,我叫林奕含。今天是个喜气的日子,所以我理应说些喜气洋洋的话,但是很不幸的,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喜气……我今年二十五岁……欸,差几天就满二十五岁了。我从高中二年级,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得了重度忧郁症,准确点来说是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了我与重度忧郁症共生的人生。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就在这上面加上了PTSD,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重郁症这件事情,他很像是失去一条腿或者是失去一双眼睛。人人都告诉你说,「你要去听音乐啊」「你要去爬山啊」「去散心啊」「你跟朋友聊聊天啊」但我知道不是那样的。我失去了快乐这个能力,就像有人失去他的眼睛,然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但与其说是快乐,说的更准确一点,是热情。我失去了吃东西的热情,我失去了与人交际的热情,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有些症状是或许你们比较可以想象的。我常常会哭泣,然后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然后我会自残。另外一些是你们或许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会幻觉,我会幻听,我会解离,然后我自杀很多次,进过加护病房或是精神病房。因为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生病的,我每个礼拜二要上台北做深度心理治疗,每个礼拜五要到门诊拿药。这就有点接近我今天要谈的精神病去污名化的核心——我是台南人,我在台南生病,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治疗我的疾病?我为什么要上台北?当然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缺课太多,差一点没有办法从高中毕业。前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好点,我就重考。这几年一直处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业的状况,前几年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去重考,然后考上了政大中文系。在中文系念到第三年的时候,很不幸的,突然开始病情发作,所以我又再度休学。在我休学前那一阵子我常常发作解离。所谓的解离呢,以前的人会叫他精神分裂,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做思觉失调。但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他,就是灵肉对立。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我才能活下去。我第一次解离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我站在离我的住所不远的大马路上,好像突然醒了过来,那时候正下着滂沱大雨,我好像被大雨给淋醒了一样。我低头看看自己,我的衣着很整齐,甚至仿佛打扮过,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的门,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对我来说,解离的经验是比吃颗止痛药,然后被推去加护病房里面洗胃还要痛苦的一个经验。从中文系休学前几个月,我常常解离,还有另外一个症状是没有办法识字。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但就是我打开书我没有一个字看得懂。身为一个从小就如此爱慕、崇拜文字的人来说,是很挫折的一件事。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然后那时候正值期末考。我的那时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过去讲话。我请我的医生开了一张诊断证明,然后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给各个教授,跟他们解释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这时候系主任与助教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助教在那边看着我,然后他说:「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啊,自杀啊,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的。」然后这时候我的系主任对我说了九个字,这九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拎起我的诊断书,问我说:「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很懦弱。我就回答他说:「医院。」但我现在想我很后悔我没有跟他说:「主任,我没有笨到在一个,活在一个对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会里,用一张精神病的诊断书去逃避区区一个期末考试。然后你问我从哪里拿到的。从我的屁眼啦!干!」我很想这样说,但我没有。所以我要问的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诊断我?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装,我的唇膏,或是我的口齿来诊断我吗?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想象是什么?或我们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然后六十天没有洗澡去找他,他就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又或者他觉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请试想一下今天你有一个晚辈,他得了白血病。你绝对不会跟他说,「我早就跟你讲,你不要跟有得白血病的人来往,不然你自己也会得白血病。」不会这样说吧。你也不会跟他说,「我跟你讲,都是你的意志力不够,你的抗压性太低,所以你才会得白血病。」你也不会跟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去注意你的白血球呢?你看你的手指甲不是长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一直去想白血球呢?」你也绝对不会这样说。你也更不会对他说,「为什么大家的白血球都可以乖乖的,你的白血球就是不乖呢?让白血球乖乖的很难吗?」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地荒谬,可是这些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听到最多的一些话。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要休学,为什么可以不用工作,为什么休学一次休学两次,然后blablabla然后没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还要不甘心。就是这个疾病,他剥削了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比如说我曾经没有任何缝隙的与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原本可能一帆风顺的恋爱,或是随着生病的时间越来越长,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去。甚至是我没有办法念书。天知道我多么地想要一张大学文凭。还有,有吃过神经类或精神科药物的人都知道,吃了药以后你反应会变得很迟钝、会很嗜睡。我以前三位数的平方心算只要半秒就可以出来,我现在去小吃店连找个零钱都找不出来。还有吃其中一种药,我在两个月以内胖了二十公斤,甚至还有人问我说,“诶,你为什么不少吃一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某一种无知,他真的是很残酷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做出任何选择。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文章,其实我从头到尾都只有讲一句话,就是:不是我不为,我是真的不能。在中文系的时候,班上有遇到一些同学,他们是所谓的文青。他们简直恨不得能得忧郁症。他们觉得忧郁症是一件很诗情画意的事情。我站在我的疾病里,我看出去的苍白与荒芜。我只想告诉他们,这种愿望有多么地可耻。我也认识很多所谓身处上流的人,他们生了病却没有办法去看病,因为面子或无论你叫他什么。我也知道有的人他生了病想要看病却没有钱去看病。比如说我一个月药费和心理咨商的费用就要超过一万台币。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想到婚礼这件事,我整天思考一些事情就是:今天我和阿帆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歌颂这个天纵英明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度。我支持多元成家,也支持通奸除罪化。我穿着白纱,白纱象征的是纯洁。可是从什么时候,所谓的纯洁从一种精神状态变成一种身体的状态,变成一片处女膜?或者比如说,人人都会说,“啊,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这句话是多么的父权。他说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不是说你美。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无论你里或外的美都要开始走下坡。意思是,从今以后你要自动自发地把性吸引力收到潘多拉的盒子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可笑。跟B在一起这几年,教我最大的一件事情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平等。从来都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学生,谁谁谁的病人,但我从来不是我自己。我所拥有的只有我和我的病而已。然后跟阿帆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他女朋友,但不是他“的”女朋友。我是他未婚妻,但是不是他“的”未婚妻。我愿意成为他老婆,但我不是他“的”老婆。我坐享他的爱,但是我不会把他视为理所当然。今天在这个场合,如果要说什么B是全世界最体贴我的人啦,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啦,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啦,然后我要用尽心力去爱他,经营我们的感情啦……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因为不然我们也不会站在这里。关于新人这个词,今天我和阿帆是新人。然后这个词让我想到我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说的新人。他常常在书里引用这个概念,就是他的书写不是写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人们的,甚至也不是写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孩,而是写给那些比最新的人还要新,给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写的。“新人”这个词出自《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叫耶稣基督为newman。所以我在想,如果今天我是新人,如果我可以是新人,如果我可以成为新人,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婚礼我就想到,我想成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有更多的想象力的人,我想成为可以告诉那些恨不得得精神病的孩子们这种愿望是不对的那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让无论有钱或没有钱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去看病的那一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实质上帮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那一种人。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知道哥哥你很爱我,我知道你最爱我,但是你不会把他说出来。我很谢谢你每天对我的关心,对我来说是我的精神粮食。然后很谢谢爸爸妈妈,虽然我没有长成那个你们从小所培育所期待,然后花很多心思所栽植的样子。没有长成那个样子,让你们失望了,我很抱歉。(林爸:不会!)我今天要讲的就这样,谢谢。年9月2日·林奕含Facebook读到所谓诗人这样写精神疾病:「握紧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伤口,他才会是真实在着且会慢慢复原的存在。」写他自己之所以不吃药因为药物跟正向思考一样都只是镇痛剂真的是去你爸的你可以不吃药只有一个原因不是你比较勇敢或比较承认你可以不吃药的原因就是你不吃不会死对不吃不会死。就这样。我十九岁开始吃思觉失调的药虽然我觉得把精神分裂改名成思觉失调仅仅像把杂货店改叫做便利商店一样徒劳且是滑稽的那种徒劳无论如何暂且叫那药X吧开始吃X之后是从十七岁生病以来终于可以感到平静的时光可以睡满八个小时可以吃完一整碗饭虽然还是噩梦虽然X的副作用让我一个月胖了二十公斤楚楚医师很开心但他知道我恨自己吹气球的身体知道我不只是照相机连车窗倒影都避讳他看我平静了一个月便说可以换药了那一个月里我还和爸妈去英国商量着留学剑桥的数学桥没有用一个钉子全是木凸榫与木凹卯衔接而成那个清纯像七夕的鹊桥像走在无限个吻之上换药之后没了X我又开始爱哭厌食幻觉幻听想自杀有一次爬出了栅字式阳台脚踩在那一横划上楼下的管理员又在看我我总不能被他看光内裤又看光脑浆终于是爬了回去楚楚要我马上住院我那时一个人住(废话不然怎么爬阳台)永远记得一个人跪在地上打包行李以前就住过的所以知道可以摔破了拿来割腕的马克杯不可以可以抽出鞋带来上吊的球鞋不可以可以在胸前插出心脏的刀叉不可以跪在那里打包换洗的内衣裤还有不知道又要住多久所以一整套带去的莒哈丝和贝克特住院之后第二次开始吃X又开始胖一吃至今一肥至今但是终于又平静下来了妈的不吃药万事万物对我而言都只是各种死法而已永远记得一个人打包一个人背着行囊办住院说是行囊但是我可以走去哪里?面对药物我确实很卑微但这跟勇气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此生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别人:它就是慢性病你不要跟我讲你糖尿病或中风了用勇气来治疗我真的恨透了这个年代所谓文青关于温柔或直面伤口的论调干这就是「房思琪」用生命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可以忘记。
不可以容忍或者原谅任何一个「李国华」。
更不可以漠视任何一个「房思琪」的发声。
唯愿天下再无房思琪。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