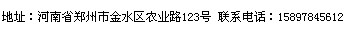骨髓瘤疾病进展与肿瘤微环境
多发性骨髓瘤(MM)是恶性浆细胞在骨髓中克隆性增生的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近年来,随着新药和靶向药物包括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单克隆抗体(CD38单抗和IgG1单抗)和免疫治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等等治疗方案的问世,显著改善了MM患者的完全缓解率和总生存,部分患者可以达到长期生存。但是迄今为止,MM仍然不可治愈,从缓解到复发、复发到难治,肿瘤细胞的恶性程度不断提升并出现对治疗药物的耐药和难治,骨髓瘤的治疗仍然面对巨大的挑战。
骨髓瘤基因组学的研究从遗传学异常分析MM的始动致癌事件以及后续继发性基因突变的发生,揭示MM疾病演变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从早期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增多症(MGUS)和冒烟性骨髓瘤(SMM)阶段已经发生始动的致癌事件,常见的如免疫球蛋白重链(IgH)的重现性易位、超二倍体和奇数染色体三倍体,随后疾病进展至症状性MM。疾病终末期浆细胞克隆侵袭性增强、可以脱离骨髓微环境而发生髓外侵犯(EMD)和浆细胞白血病。
图:MM疾病进展模式
来源:JournalofBoneOncology
骨髓瘤具备独特的骨髓微环境,骨髓中的间充质细胞、破骨细胞、成骨细胞、髓系细胞和淋系细胞是肿瘤细胞孵育的摇篮,通过直接的细胞间接触和分泌众多可溶性细胞因子调节克隆性浆细胞的迁移和归巢,形成特殊的肿瘤微环境(TME),有利于肿瘤细胞逃脱免疫监控并促进疾病进展。
骨髓瘤细胞的转运
虽然详尽的机制仍未明确,CXCL12–CXCR4轴介导了浆细胞的归巢、迁移和骨髓滞留,浆细胞可以定植于特定的骨髓龛、再循环、并从骨髓向髓外侵犯。无论是正常浆细胞还是骨髓瘤细胞都是通过骨髓窦作为进出骨髓的通道,类似于造血干细胞(HSC)进出骨髓的过程。CXCL12–CXCR4在骨髓微环境中呈高表达,CXCR4抑制剂plerixafor(AMD)可以阻断CXCL12–CXCR4轴、从而干扰MM细胞与骨髓微环境的黏附,导致MM细胞动员进入外周循环从而增加对抗肿瘤药物的敏感性。
CXCL12-CXCR4轴可以直接上调MM细胞表面α4β1整合素,使其以较高的活性与骨髓微血管上表达的配体VCAM-1相结合,该事件是MM细胞进入骨髓微环境的关键步骤,也是MM细胞再循环的关键点。除此之外,介导MM细胞归巢进入骨髓的其他重要粘附分子有α4β7整合素(MAdCAM-1和纤维连接蛋白的受体)和CD44。
P和E-选择素及其配体同样调控MM细胞与骨髓微血管的黏附作用。骨髓微血管内皮表达的P-选择素,MM细胞表面表达P-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PSGL-1),两者交联并促使恶性浆细胞沿着微血管移行。E-选择素MM归巢中的作用通过唾液酸转移酶抑制剂ST3Gal-6(产生E-选择素配体酶)以及E-选择素抗体所证实。
α4β1整合素对MM的锚定和滞留于骨髓的肿瘤微环境(TME)中起重要作用。在体内模型中已经证实,α4β1整合素依赖的MM黏附作用有助于骨髓瘤的疾病进展,其与骨髓中的VCAM-1和纤维连接蛋白相互作用可以促使白细胞介素-6(IL-6)信号激活MM恶性增殖并导致药物抵抗。
MM疾病的终末阶段,骨髓瘤细胞从骨髓移行至外周并脱离骨髓微环境而恶性增殖,可以定植于不同的器官造成髓外病变。从这个角度分析,下调CXCR4的表达可以降低MM细胞的髓内滞留。在动物模型中发现,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可降低CXCR4的表达,可能有助于骨髓中的MM细胞迁移,并促进髓外病变,这无疑是一种不被临床期望的治疗反应。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IF)也能与CXCR4结合,使其沉默而下调MM细胞对骨髓基质的粘附性,最终导致髓外病变。MM细胞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CCR1,其与循环MM细胞增多相关。CCR1的配体CCL3抑制了MM细胞向CXCL12的迁移,竞争性抑制CXCR4-α4β1轴,提示CCL3–CCR1轴可能促进MM细胞从BM外迁。
图:MM疾病进展中浆细胞迁移
来源:BLOOD
骨髓龛
骨髓龛和基质细胞
造血微环境也被称作造血干细胞龛或生态位(niche),这种特定的微环境适合HSC的生存,同时也对HSC的生长、增殖、分化以及凋亡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骨髓中含有造血细胞、非造血细胞和非细胞物质如细胞外基质(ECM)蛋白和可溶性因子等等成分,共同维持HSC池及其后代的造血祖细胞(HPC)。非造血细胞池包括间充质干细胞(MSC)及其后代间质细胞、内皮细胞、周细胞、脂肪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交感神经细胞及其相关的雪旺氏细胞。
骨髓龛分为两类,即骨内膜龛和血管内皮细胞龛,包含不同的细胞类型,表达不同的可溶性蛋白,维持和调节HSC的生长、增殖、分化以及凋亡。由于骨内膜龛血管化程度极高,因此存在重叠细胞类型。大部分HSC定位于骨髓血管内皮周围的窦状毛细血管,也是干细胞在血液和骨髓之间迁移的重要部位。目前已经确认了血管周围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几种类型,包括:富含CXCL12的网状(CAR)细胞,瘦素受体(LPR+)表达细胞,Nes-CreER和NG2-CreER细胞。这些细胞为HSC在特定龛位的定植和增殖提供关键因子,例如,CXCL12和SCF(c-kit配体),均由LPR+表达细胞和和内皮细胞分泌。
这些间充质基质细胞为HSC提供粘附分子锚,包括α4β1和α5β1整合素配体、CD44和E-选择素。同时分泌众多非HSC干细胞维持所必须的可溶性因子,如骨形态发生蛋白(BMP),IL-6,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和Notch配体,而分泌的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可以诱导HSC静止和自我更新。
HSC的后代细胞同样影响干细胞龛,包括骨系细胞、巨噬细胞和巨核细胞。骨髓骨骼干细胞(SSC)能产生集落形成单位成纤维细胞(CFU-Fs)分泌HSC龛因子包括血管生成素1、Nestin+骨髓间质细胞以及富集表达SCF或CXCL12细胞。巨噬细胞调控骨髓微环境中CXCL12的表达,诱导HSC动员,巨核细胞被证明与HSC血窦定位相关。总之,HSC与其后代细胞在可溶性因子包绕的骨髓微环境中相互叠加并相互作用。
HSCniche:由血管、神经和多种细胞组成,主要是间充质干细胞(MSC)和内皮细胞(EC),这些细胞构成并维持干细胞的微环境。
图片来源:Nature.Jan16;():-34
对于HSC龛调控除了周围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之外,还有氧张力和交感神经元。HSC龛含氧量低,导致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稳定表达,转录激活CXCL12和CXCR4的表达,从而间接促进HSC的滞留。除了血管化外,骨髓还受到交感神经支配,尤其是在小动脉旁。神经纤维和非髓鞘相关的雪旺氏细胞不仅是化疗后造血再生所必需的,也调控HSC进入血液的昼夜节律。
正常浆细胞的骨髓龛
骨髓间充质基质细胞分泌高水平的CXCL12,吸引和锚定CXCR4+正常浆细胞。CXCR4缺陷胎肝细胞重组嵌合体小鼠的浆细胞不能归巢至骨髓,成熟B细胞CXCR4缺失同样导致骨髓中浆细胞显著减少。Tokoyoda等在小鼠中采用CXCL12-GFP敲除技术证实浆细胞与骨髓间充质CAR细胞接触,这提示这些细胞构成正常浆细胞生存的生态位。其他表达CXCL12的间质细胞,如LPR+细胞、Nes-CreER或NG2-CreER细胞是否也属于浆细胞的龛位,有待进一步研究。
粘附受体有助于浆细胞附着于骨髓微血管并滞留于特点的生态位。Shp磷酸酶激活α4β1整合素,通过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促使浆细胞归巢,阻断整合素α4β1和αLβ2(也称为LFA-1)会导致骨髓龛中长寿浆细胞的耗竭。通过α4β1介导浆细胞停驻的骨髓基质细胞表达VCAM-1,纤连蛋白锚定于α4β1结合基序(CS-1)有助于骨髓龛中浆细胞的黏附和生存。
浆细胞在特定骨髓生态位的存活和增殖需要多种可溶性介质,包括IL-6和B细胞成熟抗原(BCMA)配体:增殖诱导配体(APRIL)和B细胞活化因子(BAFF)。这些介质由不同细胞分泌,IL-6主要由骨髓中的血管周细胞产生,其它间充质基质细胞和浆细胞接触时也可以表达IL-6。嗜酸性粒细胞也可以分泌IL-6和APRIL,可能是骨髓龛中浆细胞维持所必须,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嗜酸性粒细胞并非浆细胞存活所必须,骨髓中的巨核细胞同样可以产生IL-6和APRIL,支持此结论的研究发现巨核细胞缺陷的c-mpl小鼠浆细胞数量显著减少,提示巨核细胞是浆细胞骨髓生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学者认为浆细胞存活依赖BAFF–BCMA信号通路活化,但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
骨髓瘤的骨髓龛
髓外侵犯前骨髓龛
骨髓微环境不仅仅支持正常造血干细胞,同样也维持肿瘤干细胞的生长。骨髓基质细胞与基质细胞外环境吸引和维持归巢至骨髓的肿瘤细胞生存。肿瘤细胞定植后,即通过释放各种细胞因子和生长,重塑粘附受体介导的细胞-细胞接触,逐渐形成适合自身生长的局部肿瘤微环境,在此过程中无疑威胁了正常细胞群落生存。
在骨髓基质细胞基因突变的选择性压力下,骨髓的局部区域更有利于肿瘤细胞的生长。这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例如,RARγ?/?小鼠移植模型呈现MDS特征,发病机制并非来自造血干细胞固有,而是涉及TNFα促发的炎症反应,提示骨髓微环境参与了疾病始动。另一个典型案例是骨髓间充质干细胞PTPN11突变,可以促使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转化。基于IL-1β过度表达导致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生长,间充质干细胞分泌趋化因子CCL3刺激炎性单核细胞的募集。总之,骨髓基质细胞诱导的炎症性微环境有助于肿瘤细胞生长,骨髓龛中的间充质干细胞在MM细胞定植之前已经发生了遗传性突变,有助于MM细胞的存活和恶性增殖。
适合MM生长的骨髓微环境
MM细胞进入骨髓后,需要找到适合肿瘤细胞生长的微环境。尽管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存在相对独立的生态位,有证据表明两群细胞竞争性争夺造血微环境。由于富含CXCL12的环境更容易吸引CXCR4+MM细胞的定植,阻断CXCL12–CXCR4轴可以导致MM细胞释放到外周循环,因此表达CXCL12的间充质细胞,包括CAR细胞组成了MM骨髓龛龛壁。此外,与正常浆细胞相似,MM细胞通过表达α4β1、α5β1整合素和CD44锚定于骨髓龛中。
MM的病理特征是成骨细胞功能受抑,破骨细胞增殖活化促进溶骨。有人提出骨龛促进MM细胞的休眠,血管龛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近期的研究也表明:MM细胞定植和锚定于骨内膜龛中,贴近于成骨细胞,这种成骨细胞的生态位促使骨髓瘤细胞的休眠或静息状态,维持其生存。骨龛中的破骨细胞可以重塑微环境并关闭成骨细胞的触发信号,激活MM细胞再次增殖并迁移。因此,外部信号可以通过调控骨龛的生态位,唤醒休眠细胞,导致肿瘤的迁移和侵袭。包括Wnt信号通路、Notch信号通路和转录因子Runx2。
例如,DKK1(MSC分泌的Wnt途径抑制剂)在MM患者中呈现高表达,与LRP5/6受体结合阻止Wnt信号传导,β-catenin核定位,最终导致溶骨病变。此外,Wnt5同样在MM患者骨髓中高表达的一种生长因子,与其受体ROR2结合并介导MM细胞与基质细胞相互作用,ROR2缺失可导致MM细胞从其骨髓龛分离。有趣的是,抑制Notch信号可以下调CXCR4依赖的MM细胞归巢和骨髓浸润,Dll1和Jagged-1活化Notch信号通路可以通过促进MM细胞增殖而加速疾病进展。至于Runx2,MM细胞可以抑制其成骨活性、导致溶骨发生,这种抑制作用部分依赖于α4β1-VCAM-1和IL-7介导的MM细胞-成骨细胞接触。
骨髓龛的孵育
一旦MM稳定锚定后,恶性浆细胞通过直接接触基质细胞、内皮细胞或骨系细胞,或通过支持MM细胞生长的细胞因子,以及免疫逃避,重塑局部骨髓微环境,为MM进一步扩张提供刺激信号。骨髓龛逐步脱离了初始相对正常的生态位而转变为有利于肿瘤生长的肿瘤微环境,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也表现出不同于正常细胞的基因图谱。
随后,MM细胞可以远距离释放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外泌体在新的转移部位重塑微环境,为肿瘤进一步侵犯做好准备。MM细胞与周围基质细胞直接接触可以活化多种信号通路,如PI3K/Akt、MAPK、Wnt和Notch,并持续激活NF-κB信号通路,导致下游IL-6、VEGF、IGF-1和GDF15表达上调,同时抗凋亡蛋白表达上调。
参与MM疾病进展的髓系细胞
巨噬细胞
起源于单核细胞的终末分化髓系细胞,根据其功能和活化作用分为两种亚型:经典活化的M1巨噬细胞和替代活化的M2巨噬细胞。M1型分泌促炎细胞因子、活性氧和一氧化氮,同时表达MHCII型抗原。M2型包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主导免疫抑制和促进肿瘤进展,表达CD、CD、精氨酸酶,分泌IL-10,VEGF和MMP。
M1/M2的两极分化取决于环境中的激活信号:Th1衍生的细胞因子,如干扰素-γ(IFN-γ)和细菌产物,包括细菌脂多糖(LPS),促进M1分化,而Th2衍生的细胞因子如IL-10和糖皮质激素促使向M2表型分化。肿瘤细胞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产生的肿瘤细胞趋化因子,如CXCL12、CCL2、CCL3和CCL14,在体外能够促进巨噬细胞迁移至肿瘤生态位并使巨噬细胞向M2表型转化。Jak1/2信号通路抑制剂Ruxolitinib或者阻断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CSF1R)的表达可以抑制肿瘤样巨噬细胞的分化。
图:MM的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TME)
来源:Blood
数项临床研究表明,MM骨髓中M2型巨噬细胞高浸润率与较差的预后、化疗和自体移植疗效不佳相关,而M1型巨噬细胞浸润率高的患者预后较好。并且M2型巨噬细胞骨髓浸润是MM的独立预后因素,其在复发难治MM中的浸润程度明显高于MGUS、SMM和初治患者。与此指标相一致的是,血清中可溶性CD、CD、趋化因子如CCL2和MIF是与疾病进展、预后和治疗反应密切相关的生物学标志。
MM细胞与巨噬细胞的细胞-细胞接触对于巨噬细胞介导的骨髓瘤化疗抵抗非常重要,包括PSGL-1/selectins和ICAM-1)/LFA-1。巨噬细胞也参与了血管新生,VEGF和FGF-2以及促血管生成因子等可导致巨噬细胞募集和激活,形成类内皮细胞样血管结构,协助肿瘤的血管新生。此外,在体外巨噬细胞在MM归巢和迁移中发挥直接作用,并通过形成有利于肿瘤生存的免疫环境而抑制T细胞增殖。
相对应,M1型巨噬细胞则发挥抗肿瘤效应。骨髓中巨噬细胞可以作为抗原呈递细胞(APC)暴露骨髓瘤抗原,激活Th1CD4+淋巴细胞,通过IFN-γ依赖途经诱导巨噬细胞转化为M1表型。M1型细胞激活内在凋亡途径诱导骨髓瘤细胞死亡,并分泌血管抑制趋化因子CXCL9和CXCL10抑制肿瘤始动。MM细胞也可以通过调节抗原分泌从而逃避这种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监测机制。
髓源性抑制细胞
除巨噬细胞外,骨髓微环境中还存在一些髓系细胞在MM疾病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为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是一组起源于骨髓祖细胞和未成熟髓细胞的异质性细胞群体,可分为粒细胞型(G-MDSC)和单核细胞型(M-MDSC)。
与正常或者MGUS骨髓相比,MM患者骨髓中的MDSCs显著增加,同时MDSCs数量与M蛋白成正相关,经过来那度胺治疗后达到VGPR以上疗效时MDSCs水平显著降低。MDSCs参与了MM疾病进展,诱导Treg分化,抑制T细胞增殖,促进MM恶性增殖和血管新生,甚至可以分化为功能性肿瘤性破骨细胞。
MM细胞通过膜融合形成外泌体,激活STAT-3和STAT-1信号通路,上调抗凋亡蛋白Bcl-xL和Mcl-1的水平,促进MDSCs的存活。另一些研究表明,MDSCs存在可以使MM细胞分泌诸多细胞因子,如CCL5、MIP-1α和IL-6,这表明MDSCs不仅通过直接的细胞-细胞接触或外泌体途经,也可以通过细胞因子分泌促进MM疾病进展。
其它髓系细胞
包括树突状细胞(DC)、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血小板,分别以不同方式参与了MM的疾病进程。
DC作为一种抗原提呈细胞,不仅能够活化获得性免疫以促进机体对病原的清除,还能够诱导免疫耐受,维持免疫稳态。DC在不同免疫器官的定位及迁移是其发挥免疫功能和维持机体稳态的基础。从MGUS进展到MM的过程中,髓样DC(mDCs)和浆细胞样DC(pDCs)在骨髓中不断累积,但其功能受损。MM骨髓来源的pDCs不能触发T细胞增殖,同时通过分泌IL-3一方面的导致破骨发生,另一方面刺激pDCs的生存和MM细胞增殖。来源于MM患者的pDCs,IL12p70和IFN-γ迁移和分泌显著减少,这种功能缺陷涉及到IL-6的自分泌和p38MAPK信号通路的激活,两者都影响了趋化因子受体CCR7依赖的DC迁移。此外,mDCs可以通过CD80/CD86受体与在MM细胞上表达配体CD28的结合来支持MM增殖和生存。
中性粒细胞与MM疾病进展的相关性主要体现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AN)。在MM肿瘤微环境中中性粒可以异质性表现为高密度中性粒细胞(HDN,成熟阶段粒细胞),存在5个基因(CSK、GSA、MEGF、PGM1和PROK2)表达上调,与MGUS到MM的疾病进展相关。此外,MM中的HDN存在吞噬功能和氧化突发反应受损,抑制T细胞增殖,提示HDN在MM微环境中具有免疫抑制作用。
嗜酸性粒细胞与MM进展中的作用仍有争议。目前已经发现骨髓内的嗜酸性粒细胞贴近浆细胞,并且分泌可溶性因子APRIL和IL-6,它们可能参与了骨髓内的炎症反应,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与浆细胞的克隆维持相关。
肥大细胞和血小板也影响着MM疾病进展。肥大细胞一方面在骨髓中积聚显示出作为宿主反应的肿瘤杀伤作用,同时也分泌如IL-6,促血管生成新生因子等等,直接或间接维持MM细胞恶性增殖和参与骨病发生。同样,血小板在MM疾病进展过程中呈现高度激活状态,与MGUS、SMM和症状性MM的疾病进展相关。
参与MM疾病进展的淋巴细胞
Th17和调节性T细胞(Treg)在调节免疫和肿瘤中起重要作用。MM患者的外周血和骨髓中Th17细胞增多,分泌IL-17可促进肿瘤生长,但同时在长期存活(LTS)-MM患者中也发现Th17细胞数量增加。Bryant等的研究提示,Treg/Th17比值与MM疾病进展相关,MM患者Treg/Th17比值升高,而在LTS-MM患者中比值明显降低。Treg细胞可以产生TGF-β和IL-10,维持自身免疫耐受并抑制效应性T细胞增殖。
Treg在MM中的作用仍存争议,一些学者认为Treg细胞在MGUS到MM的过程中起协同作用。通过对骨髓浸润T细胞亚群分析,未经治疗MM患者中存在高频的Treg激活,并与较短的PFS相关。
小鼠的移植瘤模型中,MM细胞分泌的1型IFN介导了Treg细胞的激活和扩增,阻断IFNAR1抗体的治疗可抑制骨髓瘤的进展。此外,髓样细胞和破骨细胞分泌的APRIL可以诱导MMTreg的增殖和存活,并且在MM患者中发现的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活性增加,IDO是一种催化色氨酸转化为犬尿氨酸的诱导酶,可以导致效应T细胞功能抑制和诱导Treg分化。新近研究发现TregCD38+亚群比TregCD38-更具免疫抑制作用,在应用Dara治疗后降低,提示Dara的具有额外的免疫作用机制。
免疫检查点与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相关,PD-1和PD-L1在MM患者T细胞和浆细胞中呈现高表达。PD-L1的表达水平也是MM患者的一个预后指标。但是,抗PD-1治疗在MM治疗中临床疗效有限,与免疫调节药物(IMID)联合使用时出现严重不良事件。
自然杀伤(NK)细胞在病毒感染和肿瘤的免疫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NK对靶细胞的反应及耐受取决于不同受体对刺激和抑制信号之间平衡。NK细胞的数量在MM中仍存争议,有些数据显示MM患者NK细胞数量减少,有些研究显示NK细胞数量增加,尽管存在NK细胞的细胞毒效应的降低。MM患者NK细胞的活化受体(NKG2D、DNAM-1、CD)表达减少,CDa抑制性杀伤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表达增加。MM小鼠模型中,肿瘤恶性生长可以导致CXCR3和CXCR4/配体表达失调,骨髓NK细胞亚群中KLRG1?NK表达减少。
除上述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外,骨髓微环境中存在其它可溶性因子也可能参与MM疾病恶化。细胞外腺苷(ADO)是一种免疫抑制代谢物,其在骨髓和外周血中的水平与MM的疾病进展相关。ADO通过降低CD8+和NK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及Th1CD4+T细胞功能,增加Treg细胞的比例,从而阻碍抗肿瘤免疫反应。另一个重要的可溶性因子是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I类相关链A(MICA),其从MM细胞表面脱落而释放,可以下调NK和T细胞中NKG2D的表达,与MM患者OS和PFS相关。
骨髓微环境在MM的始动和进展至关重要。MM细胞转运和归巢受可溶性因子(主要是趋化因子,如CXCL12)以及粘附分子介导的细胞-细胞连接直接调节。一旦MM细胞锚定于骨髓龛中,MM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来改变周围微环境,这些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与骨髓基质细胞协同最终导致MM细胞滞留、恶性增殖和药物抵抗。
MM的髓外病变的机制涉及到MM细胞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或功能异常,以及独立于骨髓龛MM细胞生存因子的存在。由于抗原呈递缺陷、效应细胞功能障碍、免疫抑制细胞群增殖和高水平免疫抑制可溶性因子共同作用下,MM细胞逃避了免疫监测。靶向MM细胞和肿瘤微环境之间的分子联系,恢复免疫系统内环境的稳态,是今后骨髓瘤治疗的关键。
参考文献:
TheRoleofTumorMicroenvironmentinMultipleMyelomaDevelopmentandProgression.Cancers(Basel).
TheroleofCXCR4inmultiplemyeloma:Cells’journeyfrombonemarrowtobeyond.JournalofBoneOncology.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