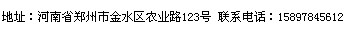化疗药有可能对孩子心脏产生毒性该如何预
在此之前,我们曾探讨了临床药物不良反应因人而异的现象(戳??吃了抗癌药以后出现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应当如何排查影响因素?)。而导致这些个体间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三类:患者依从性、临床和遗传因素。前两类易辨别与预防,而第三类遗传因素则多为未知。
遗传相关因素可导致在同样癌症诊断的情况下,不同患者即便采用相同药物治疗方案也可产生截然不同的疗效和毒副反应。
今天,我们将着重介绍药物基因组学近年来在儿童肿瘤治疗上颇有新进展的一个案例:常用广谱化疗药——蒽环类药物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作者徐佳琳医学审核
刘力维排版|博雅校对
佳妮
在儿童肿瘤治疗中可见到的伊马替尼、达沙替尼等靶向药物均为基因研究用于精准化治疗的成功案例。
药物基因组学是挖掘这些基因上的个体差异如何影响人体用药后效应的专属学科,既可以帮助预测药物治疗效果,也可以避免出现救命良药惨遭毒性或无疗效的限制。
蒽环类药物(anthracyclines)是一类临床常用的化疗药,包括多柔比星(doxorubicin)、表柔比星(epirubicin)、柔红霉素(daunorubicin)、伊达比星(idarubicin)等,主要用于治疗多种成人及儿童的急性白血病、淋巴瘤、肉瘤等各类恶性肿瘤,以及成人实体瘤,为最至关重要的化疗药物之一。
然而,蒽环类药物也可损伤心肌细胞,存在的心血管毒性往往不可逆,多数发生在用药结束后一年以上,也可出现在用药后不久。
据统计,无症状的心血管毒性发生率在用药后可最高达到57%,而在16-20%的患者中可发展成为严重的心脏毒性引起心力衰竭等。
一旦出现严重的心血管毒性,患者往往难以继续化疗而严重影响抗肿瘤治疗的整体疗效,令医生及患者面临抉择两难。
图片来源:Unsplash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
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
是否能预测或者尽早发现哪些患者更容易被蒽环类药物诱发心脏毒性呢?首先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属于剂量依赖性,用药剂量越大越容易出现。据研究结果表明,更多可影响蒽环类药物导致儿童心脏毒性的临床因素包括:
病人接受化疗前已存在心血管疾病;
年龄(4岁);
性别(女男);
病人曾经接受心脏附近(例如肺部)的放疗;
病人是否同时使用其他具有心脏毒性的抗肿瘤治疗,比如环磷酰胺、紫杉醇和曲妥珠单抗(赫赛汀);
所谓量变产生质变,患儿长期使用蒽环类药物导致累积剂量过大,也会诱发心脏毒性。
哪些措施可以预防
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
蒽环类药物在临床上已经应用了半个世纪。因此,在临床实践中,也有一些方法用来预防或减轻它们的心脏毒性。然而,这些方法并非完美。
例如,科学家研发出了一种制剂(脂质体),可以给药物穿上“隐身衣”,使它们专门攻击肿瘤细胞的同时,不会进入心脏,那么药物在心脏内的蓄积剂量就减少了。但可以想象,这些高科技“隐身衣”的价格高昂,普及面不广。
另外脂质体剂型阿霉素和柔红霉素上市不久,与常规剂型相比是否能有同等的远期疗效与不良反应仍需收集大量的临床经验后才能判断。
又如,在用蒽环类药物的同时使用右丙亚胺——一种心脏保护药物来预防心脏毒性。可是右丙亚胺在使用上也是双刃剑,虽然在国外早已被获批用于成人,在儿童人群中也有不少临床实验证明其疗效,但因其潜在的致癌性限制了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
至今,右丙亚胺仍富有争议:在欧盟,被禁用于儿童;而在北美,分析了大量儿童癌症幸存者中此项致癌性并未明显增加。
在我国,其使用需临床医生谨慎权衡利弊——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治好了一种癌症,却不得不开始对付另一种癌症。而其他保护心脏的药物在疗效上又不如右丙亚胺。
图片来源:Unsplash
更重要的是,在医生们根据已知的环境和临床因素采取预防措施的背景下,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仍然呈现出很强的个体间差异。
为什么有些患者可以承受大剂量的蒽环类药物而未出现任何心脏毒性,而部分患者即便使用了低剂量也可能产生明显的毒性反应?
所以遗传因素应该也在不良反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哪些基因
会对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
产生影响
加拿大的一群临床药理学家们找出了全球近30多年来所有与蒽环类药物相关、超过了25种基因的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哪些基因与蒽环类心脏毒性最相关,并最终总结出3组基因位点。他们发现位于三个基因(RARG、UGT1A6和SLC28A3)上的突变会影响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并由此将患儿根据其基因表达进行心脏毒性的风险分层(见下文表一)。这些突变属于一类叫做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简写为SNP)的常见遗传变异:顾名思义,就是基因序列上某一个位点的核苷酸发生改变。
SNP广泛存在于人群中,每个人体内都有四五百万个SNP,在遗传学上可以通过不同SNP的排列组合来定义一个人——宏观上,SNP会影响眼睛、头发颜色、鼻梁高度,等等;微观上,这些SNP可使得我们在疾病发生率、用药后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等方面出现千差万别。
在上述三个SNP中,前两个(分别位于RARG和UGT1A6基因上)都是危险性的,意味着携带它们的人比普通人在使用蒽环类药物后更容易出现心脏毒性;而最后一个位于SLC28A3基因上的SNP则是保护性的,即携带这个SNP的患者用药后出现心脏毒性的概率低。
表一影响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遗传变异
*危险度的测量标准是比值比(oddsratio,OR),这是一个统计学概念,以1为衡量标准:OR1时,OR数值越大,说明携带有这一变异的人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越大;OR1时,数值越小,则说明这一遗传变异可以保护携带者。危险度后面方括号内的数值代表了比值比的可信范围(统计学上叫做95%置信区间)。
#准确地说,此处应为最小等位基因频率(minorallelefrequency,MAF)。以T=2.8%为例,意味着携带有这一危险的遗传变异的人在东亚人群中占比为2.8%*2.8%+2*2.8%*(%–2.8%)=5.52%。换言之,每个患儿中就有5到6个人携带这一SNP,他们在使用蒽环类药物后就可能产生药物在心脏的蓄积,出现心脏毒性。根据严格的定义,在某一人群中MAF超过1%的遗传变异才能被称为SNP(单核苷酸多态性);在这个研究中,rs是在白人中发现的,它在白人中相对比较常见(MAF=6.4%),所以属于SNP。
这三个基因中,每一个都与蒽环类药物在体内的传输和转化密切相关。尤其是RARG,会直接影响药物在心脏中的浓度——这也就不难理解RARG基因上的SNPrs为什么危险度这么高了——携带它的患者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七倍。
图片来源:Unsplash
未来,我们将如何预防
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
基于以上结论,加拿大医务工作者们在发表研究时强烈建议所有患儿在接受蒽环类药物的化疗前进行以上三项的基因测试,并综合患儿的基因检测结果及临床状况进行心脏毒性的风险分层,根据风险高低决定不同级别的措施,从而达到有效预防蒽环类心脏毒性的目的。那些属于心脏毒性风险较低的患儿可正常使用蒽环类药物化疗、后期按常规随访;中度风险的患儿可增加随访频率,而对于高风险的患儿则建议积极使用“隐形衣”脂质体制剂,并同时使用右丙亚胺保护他们的心脏功能;用药后,对患儿的心脏功能进行更积极更频繁的检查及随访。这一项药物基因组学用于指导临床的工作已经在医院展开。截至年7月,他们已经将系列方案用于了名儿童癌症患者。
科学家和临床药理学家们将长期监测这些患儿,而我们也将持续